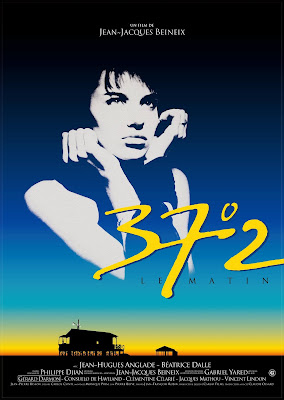|
| (時間的女兒) |
說起來,幾千年中國的皇戚諸侯彼此征伐結親的也沒少過,或許差別只在於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由秦朝底定中央集權的單一帝國模式,什麼私通燒殺都在皇帝腳下自作自受。而歐洲一直都是各自獨立的王國間愛來又亂去,單單是英國就不可和中世紀的英格蘭王國混為一談,更別提當時的歐洲各王國時而聯姻時而交戰,既有親族關係又是對立國,要搞懂真的要費很大力氣。對中世紀英格蘭有粗淺印象的人(比如說我),能夠立即想到的關鍵字大約是薔薇/玫瑰戰爭與都鐸王朝,但其實這幾個關鍵字出現時,也已相當於歐陸文藝復興時期的近代史了。